
作者:张文
引 言
笔者于本年度办理的两起商事纠纷案件,均聚焦于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这一核心痛点。第一起案例中,公司两名股东私下签订协议,约定由公司向其支付保底分红,全然不顾公司实际经营盈亏与其他股东利益;第二起案例则是全体股东达成一致约定,将公司核心资产处置后所得款项用于清偿部分股东的个人债务。两起案件的争议焦点高度重合:股东基于意思自治达成的协议,能否对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内容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究竟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则评价,还是需纳入《公司法》的规制范畴?为厘清上述疑问,笔者对股东协议的法律性质展开系统性研究。本文核心议题即在于辨析:股东协议究竟是股东之间的普通民事合同,还是可等同于公司决议的团体性文件?这一性质界定关乎股东协议的法律定位,是解决其效力边界、纠纷救济等后续问题的根本前提。
一、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的核心特征对比
股东协议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专有概念,《民法典》合同编未对其作出专门规定,《公司法》文本中亦无明确界定,本质上是对股东之间签订的、用以调整股东权利义务关系、协调公司经营运作的一类法律文件的统称。股东协议主要由长期股东签署,具体差异很大,其中一些仅涉及出资、公司设立、股权处置等事项,另有一些几乎涵盖了公司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如“一致行动”“董事、高管人事席位安排”“机构设置与职责权限”“股权回购协议”等,均属广义上的股东协议范畴。
从法律规范归属与核心特征来看,股东协议的本质契合民事合同的核心要件。李建伟教授明确指出:“股东协议的合同属性处于首要位置”【1】。《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股东协议作为股东之间就公司设立、股东出资、股权流转、利润分配、公司治理等事项达成的一致合意,完全符合这一核心定义。为进一步明晰其性质,下文将从主体、意思表示、权利义务、效力范围四个维度,对股东协议与公司决议的核心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一)主体维度。股东协议的签约主体是特定股东群体:既可以是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也可以是部分股东之间达成合意,但核心特征在于所有签约方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股东之间基于自愿原则参与协议签订,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各方在协商过程中享有平等的意思表示权,这与民事合同“平等主体之间达成合意”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
与之相反,公司决议的形成主体是公司的法定法人机关,而非单个股东或部分股东。无论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董事会决议,其制定主体均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公司权力机构或执行机构,决议的形成必须严格遵循《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式,体现的是公司的团体意志,而非单个或部分主体的个体意志。例如,股东会决议是由股东会这一公司权力机构作出,反映的是符合法定或章程约定表决比例的股东集体意志,而非所有股东的个体意志简单叠加。
(二)意思表示维度。股东协议的成立以“一致同意”为核心要件,严格遵循民事合同的意思自治原则。只有所有签约股东就协议内容达成完全一致的意思表示,股东协议方能成立;任何一方股东未认可协议内容,均会导致协议无法成立或对该未认可股东不产生约束力。同时,由于股东协议常涉及公司治理事项,其意思自治并非绝对,除需遵守《民法典》中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外,还不得触碰《公司法》中的核心强制性规范与基本原则(如资本维持原则、股东平等原则等)。例如,股东协议可约定不同于法定规则的利润分配比例,但不得约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前向股东分配利润,否则该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公司决议则以“多数决”为核心意思表示规则,这是其区别于股东协议的关键特征。公司决议的成立无需所有参与表决的主体达成一致同意,只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如股东会特别决议需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普通决议需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使部分股东或董事明确反对,决议依然可以依法成立。这一规则体现的是公司团体意志的形成逻辑,即通过多数表决机制实现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推进,而非个体意志的完全合意。
(三)权利义务维度。股东协议的核心功能是约束签约股东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规范股东内部的利益分配与冲突解决。例如,协议可约定股东之间的股权优先购买权、股东出资的时间与方式、股东退出公司的条件等,这些约定的直接约束对象是签约股东。但在实践中,由于股东协议常涉及公司治理事项,其调整范围可能出现“外溢”,不可避免地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产生影响。例如,股东协议约定董事会席位的分配规则、法定代表人的任免程序、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的决策方式等,均会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决议的核心功能则是确定公司的经营管理事项,其权利义务约束对象具有广泛性与直接性。公司决议的约束范围涵盖公司本身及全体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其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例如,股东会作出的利润分配决议,不仅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需按决议内容履行分配义务),对全体股东亦具有约束力(即使部分股东反对该决议,仍有权依据决议主张分配利润);董事会作出的投资决议,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其需按决议内容推进投资事项的实施。
(四)效力范围维度。基于民事合同的本质属性,股东协议在不涉及公司治理时效力具有相对性,原则上仅对签约股东具有约束力,不得约束未签约股东、公司及第三人。一旦股东协议是全体股东签署且涉及公司治理内容时,就不得不承担其对公司产生的约束力【2】。相比之下,公司决议则具有鲜明的团体性约束力,其效力范围覆盖公司本身及全体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一旦决议依法成立并生效,无论相关主体是否参与表决、是否同意决议内容,均需受决议约束。例如,股东会作出的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即使部分股东明确反对,仍需按决议要求履行出资义务;公司董事若违反生效的董事会决议开展经营活动,需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股东协议的双重法律属性:合同法属性与组织法属性的融合
通过上述特征对比可知,股东协议既有相对性,也有涉他性,其不仅影响非协议股东的权利,而且影响公司董事、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因此,其涉及的不仅仅是股东个人权利,而且涉及公司治理,具有契约性与组织性的双重属性【3】。这一双重属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不同适用场景下呈现不同的效力面向,共同构成股东协议的完整法律性质。
股东协议的合同法属性是其基础属性,这一点在前文已作详细论述。而组织法属性是其区别于一般民事合同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协议内容涉及公司治理事项时,可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公司产生一定的约束力,本质上是公司自治规则的补充形式。尤其在封闭性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股东人数较少、人合性特征突出,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公司经营的核心基础,股东协议常被作为公司章程的补充甚至替代工具,承担部分公司治理功能,其组织法属性更为明显。
股东协议组织法属性的核心体现为对公司治理的规范作用,具体可分为两大功能:一是程序豁免功能。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股东会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这一规定实质上承认了全体股东协议对股东会决议程序的豁免效力——此类书面协议虽冠以“协议”之名,但在满足“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针对股东会法定事项”“书面形式”三大要件的前提下,其效力等同于合法召开的股东会作出的决议,体现了组织法上的规范效果。需特别注意的是,该功能仅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资合性特征突出、股东人数较多,无法适用该程序豁免规则;同时,豁免的仅为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决议的实体内容仍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否则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
二是规则创设功能。在《公司法》允许的自治范围内,全体股东协议可创设公司章程未规定的公司治理规则。《公司法》中存在大量“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的授权性条款,为股东协议的规则创设提供了法律空间。例如,《公司法》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在此情形下,股东可通过协议约定不同于法律默认规则的利润分配比例或增资优先认缴规则,该约定若满足“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三大要件,即对公司产生约束力,公司需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股东协议的组织法属性并非绝对好处,在公司治理私序建构中使用股东协议而非通过公司章程牺牲了重要的公司法价值,包括结构性与标准化、透明度与公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公平性与平衡性。【4】
三、结论
由于股东协议的复杂性、多样性、广泛性,故对股东协议法律性质的判断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并非非此即彼的“民事合同”或“公司决议”,而是兼具合同法属性与组织法属性的双重法律文件。其中,合同法属性是股东协议的基础与核心,决定其本质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意产物;组织法属性是股东协议在公司治理场景下的延伸与补充,需满足一定的严格构成要件,在特定情形下对公司产生约束力,核心功能是补充公司自治规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股东协议以“一致同意”的民事合意为核心,公司决议以“多数决”的团体意志为核心。
本文仅对股东协议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基础性辨析,在研究过程中亦发现股东协议相关法律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与未解之处:其一,股东协议的自治边界如何界定,即“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的具体划分标准;其二,股东协议对未签约股东、公司债权人等第三人的效力范围,实践中如何平衡股东内部利益与外部交易安全;其三,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公司决议的效力等级划分,三者内容冲突时的解决规则与适用顺位。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中股东协议相关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注释:
[1]李建伟:《股东协议的组织法效力边界研究》,载《当代法学》2024年第6期,第71页。
[2]楼秋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协议效力问题研究——基于合同法与组织法交叉视阈下的效力区隔与整合》,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3]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35页。
[4]汪青松:《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5期,237页。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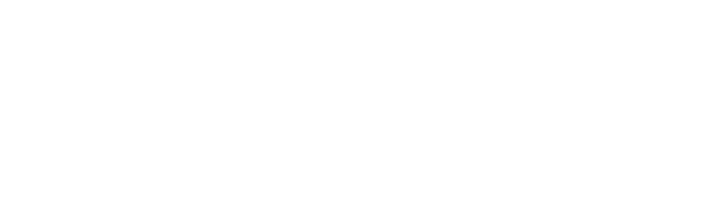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