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陆元辉
在法治社会中,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控告权,是法律赋予的重要权利,也是监督公权力运行的关键途径。但实践中,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始终存在:当公民控告渎职行为时,究竟该如何界定诬告陷害罪(下文简称“诬告罪”)的边界?本文基于法律义务的属性差异、犯罪构成证明的客观标准以及权利来源的差异性分析,认为:对控告渎职的行为,应严格限制追究控告人的诬告罪责任。
一、厘清:基于义务区分的诬告认定标准
要理解为什么不宜轻易认定控告渎职的行为为诬告罪,首先必须厘清具体罪名下被控告人法律义务的不同。诬告罪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保障公民不被错误的司法程序追究,保障司法程序的正确运行。但在这一过程中,被控告人所承担的义务性质,直接决定了诬告认定的客观标准。
1.被控告人仅承担“消极义务”的情形:
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如强奸、故意伤害),被控告人通常只有“不做某事”的消极义务。例如,被控告强奸的人,义务仅仅是“不要实施强奸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事实通常不会自然存在,只有控告人凭空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创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才构成诬告罪。
2.被控告人需承担“积极义务”的情形:
对渎职行为、律师伪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事故等特殊身份、特定行为的控告,情况则截然不同。这些被控告人不仅有不违法的消极义务,更基于其特定的身份和职业规范,负有应当如何正确履职的积极义务。
国家工作人员有依法行政、规范用权的义务;
律师有依法提供证据、参与诉讼的义务;
特种人员有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的义务。
这意味着,针对此类人员的控告所指向的“事实”,并非单纯的无中生有,而是其已经实施的、客观存在的履职行为。
这种“义务差异”,直接决定了诬告罪是否成立的客观认定标准与方法应根据不同情形进行准确区分——这一点,在控告渎职行为的场景中,尤为关键。
二、控告的三个层面:为什么控告渎职不宜轻易定诬告?
任何控告,本质上都包含三个层面,结合“义务差异”分析,就能清晰理解为何控告渎职的行为,不能轻易认定为诬告罪:
层面一:单纯的事实主张
即控告人仅口头提出事实,未提交任何证据支撑。比如控告他人强奸,仅靠口头陈述却无任何佐证——这种情况下,相关机关不会因此立案启动错误的司法程序,显然不构成诬告罪(当然可能构成诽谤罪)。
核心原因在于,这类控告针对的是“仅负消极义务”的被控告人,大多数情况下,控告事实本身无法独立存在,只能通过捏造、伪造才能形成,而单纯口头主张不足以引发司法程序的错误启动。
仍需要说明,控告渎职行为时,这种事实主张,一般应属于“无效检举”,通常连诽谤都不构成,原因在于公职人员的履职行为本就应当接受公众监督,具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
层面二:捏造、伪造证据,支撑控告事实
如果控告人不仅提出事实主张,还主动捏造、伪造证据——这种情况下,若被控告人仅负消极义务(如普通公民被控告强奸),一般就很容易认定为诬告罪,因为伪造证据的行为,会刻意创造“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进而可能误导司法机关启动错误程序。
但渎职行为的控告,即便存在伪造证据,也不能单凭这一点认定诬告:因为履职行为(如审批、执法、决策等)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伪造的证据并非决定“诬告事实是否成立”的关键——核心更在于履职行为本身是否合法。伪造材料更多只是“添油加醋”,而非“无中生有”。
层面三:对既有事实的法律评价
控告的核心争议,往往不在于“事实是否存在”,而在于“事实该如何进行法律评价”。具体到对渎职行为的控告,履职的事实本身客观存在,争议焦点在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存在过失”,这种法律评价因素的介入就会导致:
若履职行为确实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违法情形,即便控告人提交的证据有瑕疵或伪造,也因控告事实本身具有合理性,不构成诬告罪。
若履职行为经审查被认定并无不当,控告人捏造、伪造了证据,也不会必然构成诬告罪(详见下述)。
三、关键结论:认定控告渎职构成诬告罪的必要限制
1.必然的程序限制:
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这一诬告罪的定罪前提来看,对于被控告人只有消极义务的诬告而言,只要证明诬告事实不存在就无须再进行法律评价、也无须等待程序性的终局结论。
例如诬告某人强奸,只要证明控告方所讲的时间地点双方根本就没有接触,就无须再进行法律评价,除非双方确有接触、也确有发生性关系时,这时候才会涉及到对这一事实的进一步法律评价,同时还要求对于强奸不成立形成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意见。
而针对渎职行为的控告根本不可能仅凭事实证明就认定诬告成立,因为履职事实本身已经存在时,就必须要进一步评价该履职事实是否符合规范,并对此依据法定程序得出确定的认定结论。在此之前,控告是否成立不确定,当然就不能认为控告人具有意图使他人遭受刑事追究的主观故意。
2.必备的条件限制:
如前述可得出,控告渎职行为,要认定为诬告罪,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
控告人捏造、伪造了相关事实和证据;
该履职行为已经依法被确认不存在违法。
这就会导致要认定控告渎职的行为属于诬告罪,会被限制在十分有限的场景中,即通俗的讲,履职行为的违法性评价大多并非是证明违法行为存在与否的评价,而是既有行为是否合规的,关于是非对错的评价。
3.必须的关联和结果限制:
原因:为什么要评价捏造事实与诬告认定之间的关联性。
以控告强奸为例,在控告双方存在性关系情况下,构成不构成诬告,取决于这个性关系在法律评价上是不是强奸。
这种定性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强奸的法律评价即使不成立,也并不必然就能认定控告方诬告,因为这时候必须要评价所捏造之事实与诬告认定之间的关系,和基于该事实所引起的现实后果。
因为性关系发生这一的核心事实不存在伪造时,伪造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实,是否属于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肯定就需要评价这一事实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
例如控告人伪造了自己身上的抓痕以及自己醉酒被利用的事实,显然属于有诬告意图,但如果仅是伪造了使用避孕套、支付房费的事实,则不必然属于有诬告意图。
无论如何,这时候都不能轻易的认为存在伪造事实就属于情节严重,换言之,这时候就必须要考虑这一伪造事实事否具有使被控告人遭受错误追究的现实风险。
特殊性:控告渎职构成诬告的特殊性。
控告渎职的诬告认定也是同理,也应该要考虑捏造事实与诬告认定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也具有其重要的特殊性,即在事实占有和评价的优势程度上,一般而言普通公众没有能力捏造与渎职认定形成强关联的虚假事实的可能性。
例如,诬告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强拆,强拆是否合法的相关事实基本都是由行政机关掌握,这也就是在行政诉讼中,这类行为合法性证明的义务一般在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原因。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普通公民捏造的渎职证据,对于渎职事实判断以及渎职性质的评价和认定,是很难被作为是否构成渎职犯罪的事实来被司法机关对待和评价的。那么,自然就没有发生导致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实可能性。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要评价某一捏造事实的渎职控告是否构成犯罪,还必要考虑:该事实是否在渎职评价中被使用、是否可能导致渎职评价认定错误的风险。
四、限制认定根因:控告权的权利来源差异
认定诬告罪,不能忽视“控告权的权利来源”——这是区分“普通控告”与“渎职控告”的关键:
普通罪名的控告(如控告他人盗窃、强奸),控告人的权利来源,仅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救助权”或“普通公民检举犯罪的权利”;
而控告渎职行为,控告人的权利来源,除上述权利外,更核心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这是一项法定的特别权利,是公民监督公权力、遏制腐败与渎职的重要保障。
这种差异,会导致针对渎职控告的诬告认定必然有两方面的严格限制:
主观故意的证明方面:在针对普通罪名控告的诬告认定中,捏造事实本身就可独立证明意图诬告的主观故意,而针对渎职罪的诬告认定中,需要排除控告人是为正常行使监督权这一合理怀疑。
情节严重的证明方面:在针对普通罪名控告的诬告认定中,诬告事实的社会不良影响的因素可以被纳入考虑情节的严重与否的评价,但在针对渎职罪的诬告认定中不但不应简单以社会影响认定是否情节严重,而应该严格限制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也就是说,这种诬告必须要导致实害的后果,否则就可以认为相关诬告属于公职人员身份应然的被监督(检举和控告)结果。
结语
诬告罪的本质,是打击恶意干扰司法程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而非限制公民的控告权与监督权。对于渎职行为的控告,司法机关应当秉持“审慎认定、严格把关”的原则,坚持“单纯事实主张”不为罪,并利用“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评价区分的方法,严格限制诬告认定的程序要求、条件要求、关联性要求,在主观故意证明的认定中严格排除行使监督权的可能、在情节严重的证明中严格以具有实害结果为限。
唯有如此,才能在保障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监督权之间实现平衡,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公民敢于、善于通过合法途径,监督渎职行为——这,才是诬告罪立法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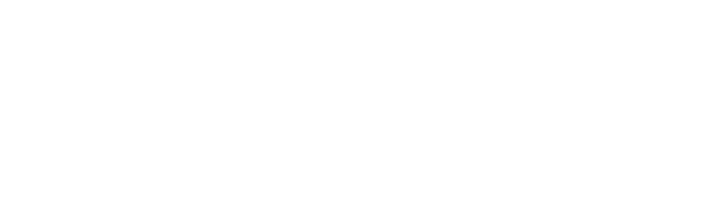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