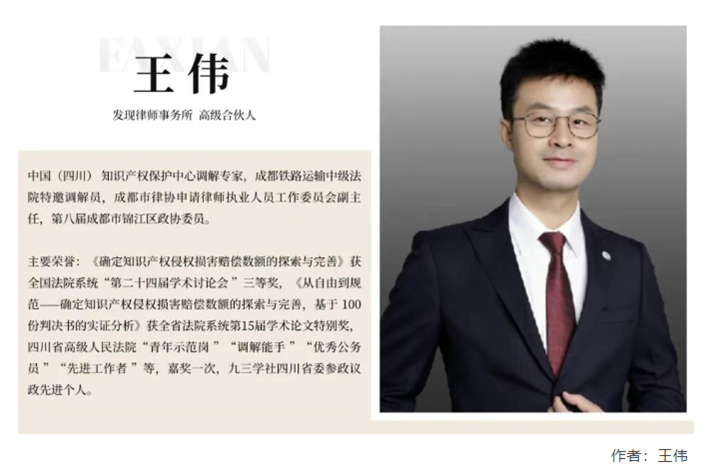
一、引言
在互联网商业环境中,企业为提升网络可见度与流量,常借助搜索引擎优化策略。其中,将他人企业名称、商标等设为搜索关键词的“关键词隐性使用”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成为司法与学界焦点。本文以威科先行网公开的24篇相关司法判例为研究样本,结合最高院“海亮案”,系统梳理当前法院认定的标准与裁判逻辑,为实务提供参考。
二、概念
关键词隐性使用指民事主体借助搜索引擎的算法,将他人具有影响力的商业标识(如商标、商号、网址等)设置为后台搜索关键词,使自身的推广链接出现在搜索他人商业标识时的搜索结果页面的行为。以(2021)京0108民初44147号上海烛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例,苏州蜗牛公司在百度搜索后台将“古剑奇谭”设置为关键词,用户搜索关键词时触发被告推广链接,但链接内容与关键词无直接关联,前端推广链接标题及描述中仅显示“经典武侠【蜀门】...”并标注“广告”字样,即属于典型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 与直接在网页内容或广告中使用他人商业标识的显性使用不同,关键词隐性使用在用户可见的搜索结果页面无明显标识,仅通过后台设置实现,因此其具有隐蔽性,常见于同业竞争企业间为争夺市场份额,通过设置关键词将本可能流向竞争对手的潜在客户引流至自己的广告链接中。 因其使用方式未在商品或宣传中直接展示商标、未发挥识别来源功能,不属于《商标法》第48条[1]规定的商标性使用,故关于“关键词隐性使用”不构成商标侵权已经渐渐成为实务界的共识,该观点在(2023)沪0114民初16434号、(2023)闽01民终5540号、(2018)沪0115民初87336号等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三、争议
目前尚存的争议在于,“关键词隐性使用”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在2025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第7条第2款对搜索关键词使用问题做出单独规定的背景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虽然新法明确了以“引人误认”为核心的搜索关键词区分治理方案,但仍有一些观点认为立法者并没有排除可以援引“反法”一般条款对被诉行为予以二度评价。即,有观点认为,“设置搜索关键词”行为即便没有构成“反法”第7条之混淆,但如果行为人违背商业道德,恶意搭他人便车,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依然可以依据“反法”第2条的规定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实务中大多数法院也是如此判决的。 四、判例
在威科先行网以“隐性使用”、“关键词”检索到的24篇有效判例(无四川地区的案例)中,仅6篇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占25%),18篇认定构成(占75%)。这一比例既反映了最高院“海亮案”对下级法院的指导作用,也体现了基层法院的裁判智慧——法院普遍采取“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被告无恶意,否则倾向于认定构成反法第2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但辅以较低赔偿额”的裁判逻辑进行利益平衡,并且这种倾向在近年来越来越明显。下文将分别解析两类判决的特征与裁判逻辑。 (一)支持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例
通过对近年来十六起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可得出法院在认定关键词隐性使用构成不正当竞争时,表现出具有一定共性的认定规则,以下对法院的裁判共性进行一定总结。 1.构成要件的认定 主体层面,法院认为,无论当事人处于直接同业竞争还是广义市场竞争范畴,只要存在客户群体重叠或服务内容交叉(如游戏运营商、APP开发者、加盟服务平台等),即满足竞争关系要件。如在(2024)京73民终2005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双方均属游戏相关服务提供者,存在广义竞争关系”,突破了同业限制。 主观层面,“明知而故意”成为核心认定标准。多个裁判文书都强调,被告作为市场参与者,对原告商标或名称的知名度具有明确认知。例如(2023)沪0114民初16434号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明知原告商标知名度,仍将涉案关键词用于竞价排名”,这种有选择性地将他人高知名度标识设置为关键词的行为,被评价为具有攀附商誉、搭便车的主观恶意。 客观行为的不正当性则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证成:其一,技术层面利用关键词与展示内容的关联机制,将搜索原告的精准流量导向自身平台;其二,行为缺乏技术必要性,纯属谋取不当竞争优势的工具;其三,行为本质系对他人商誉的寄生性利用,损人利己。值得注意的是,(2023)京73民终2005号、(2021)京0108民初44147号、(2020)粤73民终805号、(2020)粤0106民初39540号、(2018)沪0115民初87336号案例中,法院都明确否定了“行业惯例抗辩”,即“关键词推广是搜索引擎广告常规模式”并不能成为有效的抗辩理由,普遍违规不能使个体行为的不法性正当化。 损害后果层面,法院倾向采用务实而灵活的认定标准。最直接的损害表现为交易机会的剥夺,即本应属于原告的潜在客户被系统性分流。值得关注的是,多个判决如(2024)京73民终2005号明确表示无需实际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只要存在截流可能性即构成损害。同时,法院还会考虑此类行为是否会导致消费者搜索成本的增加,如果用户需耗费额外精力辨别广告与自然搜索结果,法院也会倾向于认定其造成了一定损害,如(2023)沪0116民初15014号就指出被告的行为“增加了用户的搜索分辨成本”。此外,还有的法院会将市场整体的公平性是否受到影响纳入考虑,如最高院在(2022)最高法民再131号“海亮案”中将损害后果上升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认为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损害,显著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之规定。 2.赔偿数额的认定 关键词隐形使用案件中,原告一般会主张“经济损失X万元”及“维权合理支出X万元”。对于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因原告实际损失与被告侵权获利普遍难以精确计算,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商标知名度、行为性质(主观恶意程度、手段隐蔽性)、持续时间及推广排名位置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额,如(2023)京73民终2951号案中10万元赔偿即基于多重因素权衡。关于维权合理开支的认定,公证费法院通常全额支持,律师费则需提供票据充分举证或由法院结合案情酌定。就现有公开的判例来看,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普遍不会全额支持,都会打一定折扣,就现有公开的判例来看,打五折居多。 综上,上述裁判逻辑可凝练为:同业竞争关系+明知知名度+故意攀附+关键词截流+竞争利益损害/市场秩序扰乱+违反诚信原则=不正当竞争。 (二)不支持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判例的特征
在关键词隐性使用引发的纠纷中,尽管部分案件被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案件经司法审查后被排除在侵权范畴之外。通过对六起典型裁判的梳理,法院在否定不正当竞争成立时呈现出清晰的共性逻辑,其裁判要旨集中于主观恶意的证据缺失、行为性质的技术中立性、损害结果的不可归责性等维度。 主观层面,缺少攀附故意的证据成为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关键要素。法院通过三重标准审查主观状态:首先考察关键词设置内容,若仅为行业通用词(如“手游”、“软件”等)则排除恶意推定;其次检视当事人的态度,如(2023)沪0109民初3915号案中被告“收到投诉后立即删除关键词”被视为当事人善意;最后审视关联行为性质,如(2021)京0108民初17480号案明确:若存在将他人商标加入网站“源代码”等行为则可能推翻中性评价。这种分层审查机制,有效防止了将技术必要操作泛道德化为“搭便车”的意图。 客观行为层面,法院在否定侵权认定时,尤为重视案件中的技术使用手段是否具有中立性。在(2023)粤73民终1888号案中,二审法院推翻一审判决的关键在于查明被告仅设置“手游”等通用词汇,而搜索结果出现“小7手游”关联链接系搜索引擎算法动态匹配所致。法院明确指出:“百度推广结果依赖AI动态匹配…非推广方主观控制”,并辅以行业普遍现象佐证(如搜索“0元手游”亦出现“小7手游”链接)。同样,(2023)沪0109民初3915号案强调苹果应用商店关键词机制属“平台固有运营机制”,被告行为符合技术场景的合理使用范畴。此类裁判将算法自动生成结果与经营者主动干预严格区分,避免将技术固有特性错误归责于市场主体。 损害后果层面,无法证明实际损害后果构成否定侵权的另一核心要素。法院要求原告须完成两重举证责任:其一需证明用户混淆或交易机会被实质性剥夺;其二需证明损害与被告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联。(2021)京0108民初17480号案中,因隐性链接位于搜索结果末尾且原告官网占据自然结果首位,法院认定“消费者未被误导”;而(2017)苏民申2676号案更直接指出“原告未举证实际损失(如流量减少、交易机会丧失等)”。尤为典型的是(2023)闽01民终5540号案,原告虽证明“某某丁”在餐饮类别的知名度,但未能举证其在软件领域的市场影响力,导致法院认定“相关公众不会误认双方存在关联”。此类裁判凸显司法对损害事实客观性与因果关系严密性的严格要求。 此外,法院还会对标识是否具有显著性进行一定的考量。在涉及未注册商标或特定名称的案件中,标识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裁判结论。(2021)京0108民初17480号案揭示:即使原告“瑞达恒”具有知名度,但因“RCC”未单独发挥标识功能,故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服务名称”。类似地,(2023)闽01民终5540号案区分商标核定类别,指出餐饮类商标知名度不能自然延伸至软件领域。此类裁判有利于防止商业标识保护范围的不当扩张。 综上可知,无攀附故意(及时修正/无关联行为)+技术中立性(算法自动匹配/行业通用词)+损害不可证(无实际混淆/无交易机会剥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五、结论
通过对24篇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可见,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在司法实践中并无统一的答案,其认定依赖于个案的具体事实和证据。 法院的核心审查逻辑聚焦于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是否存在攀附故意)、行为的客观表现(是否具有不正当性、所利用技术是否具有中立性)以及损害后果(是否实际或可能造成竞争利益损失或扰乱市场秩序)三个关键维度。 尽管2025年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2款为规制搜索关键词混淆行为提供了明确依据,但司法实践表明,对于不构成混淆但可能违背商业道德的关键词隐性使用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一般条款仍扮演着重要的补充性规制角色。当前判例显示,司法实践对关键词隐性使用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持审慎态度,最高院“海亮案”确立的“实质损害”标准与基层法院的“低额判赔”模式,共同构建了“既规制恶意搭便车,又保障竞争自由”的平衡框架。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在利用关键词推广策略时,应着重评估所选用关键词的关联性,避免刻意选择竞争对手的高知名度标识,以有效规避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风险。
注释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