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刑辩 || 浅析如何把握近亲属收受财物认定共同受贿的问题

关注发现,认识更多有温度、有灵魂的法律人


一、前 言
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共同受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探讨的热点,特别是关于近亲属这一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成立共同受贿的问题,实践中存在认识不一致、适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因而经常产生争议。现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谈谈笔者的理解和看法,供大家讨论和参考。
二、法律依据
关于近亲属构成共同受贿的问题,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和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先后作出了规定,因内容上存在重合和不一致的地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
(一)《纪要》和《意见》的相关规定
1、《纪要》第三条第五项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2、《意见》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二)《纪要》和《意见》的分歧与分析
1、《纪要》在关于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的问题上,未明确使用“通谋”一词,而是规定了两种情形。实践中有学者认为,按照《纪要》规定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不需要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具备“通谋”,只需要满足该两种情形即可。而按照《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含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需要具备“通谋”。
2、从范围上看,《意见》规定的特定关系人实际包含了《纪要》规定的近亲属,因此在近亲属构成共同受贿的问题上,就存在规范性文件交叉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根据《纪要》规定,近亲属构成共同受贿分为告知型和明知型,其特点有:①要求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②要求近亲属收受财物,也就是说《纪要》关于近亲属构成共同受贿明确要求了近亲属需转达请托事项。而《意见》规定,特定关系人(含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需具备“通谋”,内容包括近亲属收受财物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两方面,但没有规定一定要转达请托事项。
3、实践中对“通谋”的理解存在差异,包括“两高”的相关人员也有不同的解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人员的解释,所谓“通谋”,是指共同谋划,也即在实践中认定“通谋”不能仅看是行为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内心认识,还必须考虑双方真实存在的交流互动,也就是把“通谋”以某种客观形式展现出来。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则认为,“通谋”应指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受贿主观故意的达成,是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行为要求,因为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双方通过暗示或默示的方式,完全可以达成通谋,因此通谋的形式并不重要。
以上分歧,经常成为实务中讨论的热点和焦点。实践中又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近亲属没有转达具体请托事项,也不知道具体请托事项,只实施了收受财物的行为,应如何适用规范性文件?又该如何进行认定?
三、笔者理解
(一)要正确处理《纪要》与《意见》的关系
1、《意见》发布后,《纪要》并未废止,二者均为现行有效解释。《纪要》关于近亲属成立共同受贿所作的两类规定,实际上属于注意性规定,并非创设新的认定标准,该两类规定针对的是当时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的两种情况,为了统一认识,才以列示方式写入《纪要》,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纪要》关于近亲属成立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仍应以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具备“通谋”和“实行行为”来判断。
2、《意见》制定后,有意见认为对近亲属(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共犯的认定应以《意见》为准,但《意见》对“收受财物”的规定又太过狭窄,对传统的受贿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受贿形式无法涵盖,可能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对这一点,笔者认为不能以点盖面,《意见》所做的这些规定,实际是为解决当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受贿而作的特别规定,因新型受贿的形式较为复杂,隐蔽性极高,为避免打击面过度扩大,《意见》对《纪要》的规定进行了适当缩限:一是将“非国家工作人员”限定为“特定关系人”,包括近亲属、情妇(夫)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二是将收受财物的方式限定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即交易差价、干股分红、合作投资、委托理财、挂名领薪等10种具体形式。虽然近亲属成立受贿共犯的问题在某些规定上《纪要》和《意见》确实存在重合和衔接不理想的情况,但二者的适用关系,还是应当借以“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对新型受贿犯罪优先适用《意见》,对其他类型的贿赂犯罪,适用《纪要》的有关规定。
(二)要准确把握“通谋”的实践认定
1、如前所述,《纪要》关于近亲属成立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仍应以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具备“通谋”和“实行行为”作为判断。而《意见》也要求近亲属主观上要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通谋”,客观上要“共同实施受贿行为”,因此二者在规定的内涵上具有一致性。
2、实践中对近亲属是否收受他人财物的认定较为简单,但对双方“通谋”的认定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复合型犯罪,其实行行为包含了“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两方面,因此认定“通谋”,需要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在“为他人谋利”和“收受财物”两方面均具有意思联络,如果行为人仅单纯的接受贿赂,而对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的事实不具有认识,则不能认定二者具有“通谋”。笔者认为此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据相关司法判例的研析看,实践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意思联络”不能限定为知晓具体谋利事项或谋利的过程和结果,而应以国家工作人员和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对彼此实施的“实行行为”具有认识即可,即近亲属知道财物是谋利事项的对价,能够认识到权钱交易的本质即可;二是对“认识”可做概括性理解,即在实践中能够通过一定的事实要素,作出合理推定即可,因为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是亲密的利益共同体,二者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彼此信任,所以很容易通过暗示或默示的方式达到“认识”,但如果推定的事实毫无根据,则不能认为具有“认识”。
综上所述,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对所收受财物性质的明确认识和存在“通谋”,是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的两个必备条件。如果不能证明近亲属有参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意志因素,根据现有规定,不能构成共同受贿。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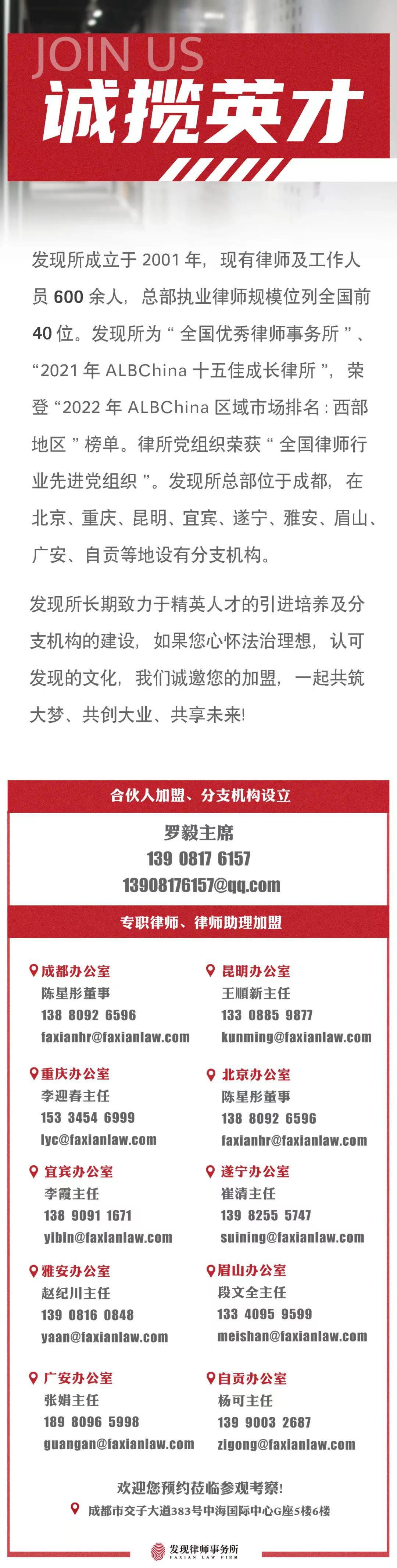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