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刑辩 || 浅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犯罪主体

关注发现,认识更多有温度、有灵魂的法律人


近日,笔者作为辩护人代理了一件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案件,简要案情系:当事人甲系某国有控股公司(简称A公司)副总工程师、A公司某分公司经理,其与A公司董事长乙及其他社会个人股东成立B公司,经营与A公司相同业务,并利用乙的职务便利,安排A公司为B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检察机关已对甲以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提起公诉,并认定甲为与乙共同犯罪的从犯。通过代理本案,引发了笔者关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犯罪主体的思考。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从立法意图来看,本罪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最大化,防止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违反竞业禁止性规定经营同类营业谋利,造成的国有公司、企业利益受害。因此本罪的主体应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但关于国有公司、企业外延,董事、经理内涵,以及一般主体是否构成共同犯罪,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一、“国有公司、企业”是否包括非全资国有的国家出资企业
有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包括全资国有企业及国有参股企业;也有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仅限于国有全资公司,而不包括非全资国有的国家出资企业。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第六条规定,“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虽然该意见并非专门针对《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作出,但意见将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分列,可见国有公司、企业与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不同,仅指全资国有公司、企业,而不包括非全资国有的国家出资企业。
二、“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是否特指《公司法》中的董事、经理
董事是指公司、企业董事会的成员或者执行董事,一般较易区分,在认定其身份上不存在争议。但经理称谓在公司中的职务则比较广泛,有的公司将其中层管理人员也称作经理,如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执行经理等,也有公司将分公司负责人称作经理,比如本案中的当事人甲。笔者认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特指《公司法》中的经理,而不包括其他经理称谓的人员。《公司法》中的董事、经理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负责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掌握和影响公司经营决策、经营方向、经营效果的职权,《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对公司董事等高管人员竞业禁止作出了规定。而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执行经理或者分公司经理等经理称谓人员,往往经营管理权有限,只负责特定业务的经营管理,《公司法》亦未对其作竞业禁止性规定。因此,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不应扩大至《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经理外的其他管理人员。
三、“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是否特指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董事、经理
随着国有企业混改的进程,具有行业优势经验的民营企业与具有平台优势的国有公司、企业进行合作,成立国有出资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国有出资公司中往往同时存在国有公司、企业派驻高管及民营企业派驻高管,对于上述高管人员经营同类业务的行为,能否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进行定罪量刑,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董事、经理,而不包括国有出资公司的董事、经理;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不应机械解释为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董事、经理,而应当与时俱进进行解释,包括国有出资公司的特定董事、经理。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解释》(法释〔2005〕10号)明确,“为准确认定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现对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解释如下: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该解释直接适用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扩大了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外延。既然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那么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从事公务的董事、经理,也应当以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第六条规定,“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的同时,也将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范围再次扩大。至此,“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不局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董事、经理,也包括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国有出资公司中从事公务的董事、经理,甚至包括“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董事、经理)”。
在具体主体身份认定上,应当注意以下事项:一是受委派的主体只能是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其中“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包括公司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如系受民营企业委派则不符合;二是行为人应受委派从事公务,即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如果只是从事一般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则不属于从事公务。
四、非特定身份主体是否能够成为共同犯罪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系身份犯,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能否与具有身份的人员构成共同犯罪,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即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该条款系对不具有特定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贪污犯罪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条款确定的原则能够适用于其他特定身份犯罪。比如,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原则上应为男性,但女性协助男性强奸亦可构成强奸罪的共犯,同理,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与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共谋,利用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身份便利经营同类营业的,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员可以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共同犯罪。
●●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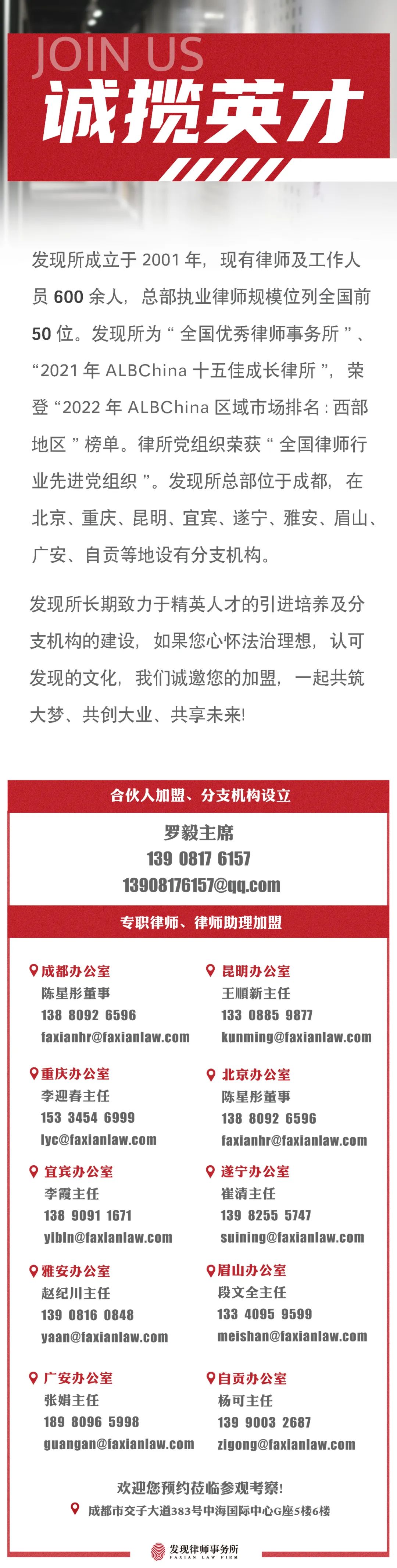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