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左青青
引 言
司法实践中,同一事实常同时引发刑民责任,“合同涉刑”尤为典型,如假借买卖合同诈骗、高管以单位名义签约后侵吞款项、合法借贷资金被用于非法活动等。此类案件中,刑民程序交织,合同效力成为争议焦点。
然而,实务中常将“行为构成犯罪”简单等同于“合同无效”,既混淆了刑民规范逻辑,也易损害交易安全与善意相对人权益。厘清刑事犯罪对合同效力的具体影响,对律师代理刑民交叉案件、评估风险及制定应对策略具有直接实务价值。
一、刑民分立:评价体系与立法宗旨的根本差异
刑法与民法虽同属法律体系,但在立法宗旨、调整对象与评价标准上存在本质区别。
刑法以“惩罚犯罪、保护法益”为核心,聚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判断其是否符合特定罪名的构成要件。一旦行为构成犯罪,即应承担刑事责任。
民法则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与人身关系”为基本任务,强调意思自治、诚实信用与交易安全。合同是平等主体依自愿、公平原则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其成立需经要约、承诺乃至履行等环节。法院在判断合同效力时,关注的是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由、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非行为人是否涉刑。
以合同诈骗罪为例:刑事审查聚焦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并造成财产损失,评价其是否应受刑罚;民法则关注契约行为是否体现当事人真实合意,是否应赋予私法效力。概言之,刑法评价缔约手段的刑事违法性,民法判断缔约结果(即合同)的民事效力。
二、合同效力应依民法独立判断
“合同当然无效说”曾长期主导理论与实务。然而,即便同一行为已被刑事司法认定为犯罪,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仍须回归《民法典》规范体系独立判断。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吴国军案”中,法院指出,借款行为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效力认定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亦在其调研报告中强调,即便同一事实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合同效力亦不宜一概而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13条明确规定:“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已被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该条确立了“刑民责任区分”与“合同效力独立判断”原则,为处理此类交叉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引。
三、合同效力的民法判断路径:回归规范本体
刑法与民法虽各自规制行为,但均未就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标准作出直接规定。刑法规范难以作为民事合同效力的判断依据,合同效力只能以民法规范为直接准绳。鉴于合同效力形态多元、罪名类型繁杂,且不同犯罪对合同影响各异,涉刑合同可能有效,也可能存在效力瑕疵。
《民法典》将合同效力规则由原《合同法》整合至“总则编”第六章,基本延续《民法总则》规定,并作出三项重要调整:一是删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欺诈、胁迫损害国家利益”作为无效事由;二是新增“虚假的意思表示”为无效情形;三是将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统一纳入可撤销合同范畴。
根据《民法典》第144–154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包括: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4条);
虚假的意思表示(第146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153条第1款);
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第2款);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154条)。
此外,第147–151条规定了因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情形下的可撤销合同制度。
在涉刑合同案件中,第153条(尤其是第2款“违背公序良俗”)与第146条(通谋虚伪表示)最为常用。但需注意,并非所有犯罪行为均必然导致合同违背公序良俗。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指出:犯罪行为虽具违法性,但若未实质性影响合同意思表示的核心环节(如缔约目的、内容或方式),则不应仅因存在犯罪行为而否定合同效力。
换言之,民法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紧扣该法律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有效,而非将行为人因其他违法犯罪所获的整体可责性,直接移植至民事评价。
四、涉刑合同效力的判断框架:目的—阶段—主体三要素
对涉刑合同效力的判断,应摒弃“一刀切”思维,构建一个由合同目的定性、行为阶段定位、责任主体归责组成的三层分析框架。
(一)目的定性:合同目的与犯罪行为的关系
判断涉刑合同效力的逻辑起点,在于考察合同目的与犯罪行为的内在关联。司法实践中通常区分以下四种情形:
1.合同内容本身即构成犯罪
如买卖毒品、枪支、人口或伪造货币等,其标的直接违反刑法禁止性规定,合同目的非法,应依《民法典》第153条认定为无效。
2.合同系实施犯罪的工具
如虚构投资项目诱签“投资协议”以骗取资金。此时合同虽形式合法,但缺乏真实交易意图,可能构成第146条的“通谋虚伪表示”(表面行为无效);即便不构成通谋,因其目的严重背离公序良俗,亦可依第153条第2款认定无效。
3.犯罪与合同仅有间接关联
如公司高管以单位名义签订合法购销合同后侵吞款项,构成职务侵占罪。因合同目的合法、内容合规,且相对方善意无过失,犯罪行为发生于履行阶段,不影响合同效力。单位仍应依约承担责任,损失可向行为人追偿。
4.利用合同结果实施犯罪
如通过合法房屋买卖取得款项后用于洗钱。只要缔约时意思真实、目的合法,后续资金用途违法不具溯及力,合同应认定为有效,犯罪行为另行追究。
(二)阶段定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
犯罪行为介入合同关系的时间,直接影响效力判断:
订立阶段(如欺诈、胁迫):破坏意思表示真实性,构成《民法典》第148条(欺诈)或第150条(胁迫)规定的可撤销事由,赋予受害方撤销权。
履行阶段或之后(如履约后侵占、挪用):合同已有效成立,后续犯罪属权利滥用或独立侵权行为,一般不否定合同效力,仅引发违约、侵权或追赃问题。
此区分体现民法对既成交易秩序的尊重,避免因事后违法行为动摇前端民事关系。
(三)主体归责:责任主体分离时的法律适用
当“犯罪行为人”与“合同当事人”不一致时,需借助民法代理规则确定责任归属:
1.若二者同一(如自然人个人诈骗),责任主体清晰,刑民责任可分别追究。
2.若二者分离(如员工以公司名义签约后犯罪),则需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
《民法典》第170条规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第172条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见代理成立,法律后果由单位承担。因此,即便行为人构成犯罪,只要符合职务外观或表见代理要件,单位仍可能承担合同责任。该规则既保护交易安全,亦倒逼单位加强内部风控。
综上,涉刑合同效力的审查,是以“合同目的”为原点、“行为阶段”为纵深、“责任主体”为落点的系统性判断过程。
结 语
刑事犯罪与合同效力的关系,绝非“一罪否全”的简单逻辑。刑法的否定评价不必然传导至民法领域。民法应坚守其独立价值——保护交易安全、维护意思自治、区分善意与恶意。唯有在尊重刑民分立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合同目的、行为阶段与责任主体等要素进行精细化判断,方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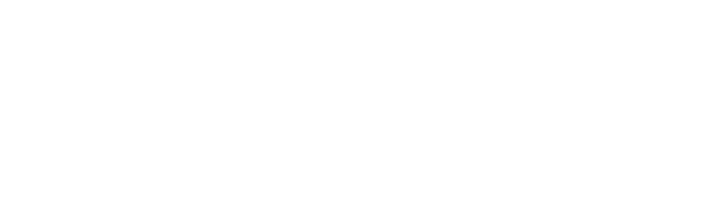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