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I公司主体股权交易风险:解析境外证据适用诉讼程序细则 || 再审研析

关注发现,认识更多有温度、有灵魂的法律人
再审研析栏目,聚焦最高法院和四川高院再审案例,研析裁判要旨,启迪办案思路,每周三在这里与您准时相约。
本期作者:罗毅、夏冬
世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随着我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深度参与全球化治理,部署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业迫在眉睫。本文由涉BVI公司股权纠纷的案件引入对境外证据适用诉讼程序的概述和实务建议。
一、案情简介
UPBEAT公司系注册在BVI(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法人,股东为陈志诚及其亲属等人。
虹桥会所系1994年12月成立的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方为UPBEAT公司,名下拥有伊犁路XXX号土地。依据2015年7月7日的房地产权利限制状况查询结果,该处房产已被采取多项查封司法限制措施及部分房屋被设立抵押。
2005年7月11日,虹桥会所、UPBEAT公司为甲方、廖东汉为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愿将全资(100%)所有的虹桥会所股权中的50%出售予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自然人和法人,协议确定买卖标的物的主要财产位于上海市伊犁路XXX号,买卖金额为8000万元;协议还约定,虹桥会所的董事长由甲方推荐,副理事长由乙方推荐,待乙方给付本协议书第四期款后,改由乙方担任董事长,甲方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并经虹桥会所董事会同意的专业经理人担任。《协议书》签订后,陈志诚及其亲属将UPBEAT公司50%股权变更至廖东汉及其亲属名下。
虹桥会所2005年8月26日公司章程以及2009年8月22日公司章程第二条关于“投资方的介绍”均载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
2009年12月7日,廖东汉依据《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以虹桥会所和UPBEAT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贸仲上海分会申请仲裁,提出要求虹桥会所及UPBEAT公司恢复廖东汉在虹桥会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的身份等仲裁请求。
贸仲上海分会于2011年1月31日作出(2011)中国贸仲沪裁字第033号裁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均认可在履行2005年7月11日《协议书》过程中,通过事实行为对股权转让交易架构作了变更,即转让标的由原先合同约定的虹桥会所50%的股权变更为UPBEAT公司50%的股权,股权转让的当事人由原先合同约定的UPBEAT公司与廖东汉及廖东汉指定的自然人和法人变更为廖东汉及其亲属与陈志诚及其亲属。仲裁庭认为,股权转让标的和当事人的改变不会影响当事人履行《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最终裁决虹桥会所与UPBEAT公司共同配合立即履行恢复廖东汉担任虹桥会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的义务,虹桥会所依据《协议书》规定履行选任总经理的职务义务。
2010年4月22日,上海胡光律师事务所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刊登“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重大法律风险提示告知书”。海胡光律师事务所代表廖东汉先生就上海虹桥会所有限公司经营、管理权争议及其相关重大法律风险作出公告如下:因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陈志诚的任职违反合同约定且程序存在瑕疵,公司经营、管理权归属亦存重大争议,廖东汉先生已于2009年12月依法申请仲裁。本律师事务所现向社会公众作出法律风险提示,望各界人士充分注意公司目前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在未经廖东汉先生同意前避免与之发生合营、承包、兼并、资产出售等一切重大交易行为。罔顾公告内容而作出的前述行为均将被视为无效。
2011年3月2日,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甲方)与国鸿公司(乙方)签订《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100%虹桥会所股权转让予乙方;乙方收购虹桥会所总价款为8000万元;股权转让完成后,虹桥会所的债权债务继续由虹桥会所承担。2011年5月,经行政审批,虹桥会所的股东由UPBEAT公司变更为国鸿公司。国鸿公司及陈志诚均确认,国鸿公司已将《收购股权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8000万元支付至陈志诚指定的账户。
2012年6月11日,陈志诚向廖东汉、廖炳耀等邮寄通知书,称UPBEAT公司投资控股的虹桥会所股权及营业权全部出售予国鸿公司,对价为8000万元,并由受让人概括承受虹桥会所之一切债权债务。
目前,UPBEAT公司股东中,陈志诚持有UPBEAT公司50%股权,廖姓以及与廖姓有关的股东,包括廖炳耀、荣思公司、御智公司、汇新公司,共持有UPBEAT公司50%股权。UPBEAT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虹桥会所股权全部变更至国鸿公司名下后,UPBEAT公司无其他资产。
2009年10月下旬虹桥会所改由陈志诚接管,同时虹桥会所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的账册由陈志诚保管。
由于廖炳耀对2009年3月23日后陈志诚方签署的UPBEAT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了异议,廖炳耀作为原告在BVI法院以UPBEAT公司为被告提起了有关诉讼。廖炳耀陈述其已经收到了诉讼结果,其有关确认2009年3月23日后陈志诚签署的UPBEAT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请求得到了BVI法院的支持,且该判决已经生效。但由于判决书中文字表述问题,该判决未能取得中国大使馆的认证。
廖炳耀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确认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2011年3月2日签订的《收购股权协议书》无效;判令国鸿公司与虹桥会所共同配合,将虹桥会所100%股权恢复至UPBEAT公司名下。
二、一审裁判
(一)廖炳耀作为UPBEAT公司股东有权提出确认案涉《收购股权协议书》无效之诉。廖炳耀称陈志诚与国鸿公司恶意串通将虹桥会所的股权低价转让,导致UPBEAT公司资产减少,进而影响到第三方廖炳耀作为UPBEAT公司股东的利益,故其以原告身份将《收购股权协议书》签订双方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因廖炳耀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故廖炳耀系本案适格原告。
(二)陈志诚出面代表UPBEAT公司签署了《收购股权协议书》,此举未征询其他廖氏股东意见,不影响该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的问题。虹桥会所的公司章程中关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表述表明,UPBEAT公司认可陈志诚为董事局主席,且其职权范围与法定代表人相同。由于陈氏和廖氏各占UPBEAT公司50%股份,在签署《收购股权协议书》时,并无证据反映陈志诚征求了廖氏股东的意见,即未取得超过持股50%比例以上的UPBEAT公司股东的同意,但是即便如此,也是陈志诚相对于UPBEAT公司股东意志而言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作出转让虹桥会所100%股权决策的公司法上问题。
至于是否影响其对外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由于陈志诚在签署协议书时,具备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身份证明文件,该文件又存档于我国国家工商行政机关,具有公示作用,证明文件中廖氏对陈志诚的董事局主席身份予以了授权,并且陈志诚在《收购股权协议书》上不但签名,还加盖了UPBEAT公司的授权签字印章,即其系代表UPBEAT公司签署的文件。国鸿公司此时有理由相信陈志诚有权对外代表UPBEAT公司签署该协议书。
事实上,协议书所涉股权已经完成了相关审批和变更登记。现廖炳耀以UPBEAT公司内部未形成有效决议为由对抗外部受让人国鸿公司所签署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不具备合同法上的依据,也不利于维护股权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
(三)陈志诚出面代表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签订的《收购股权协议书》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廖炳耀利益的情形。
首先,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股权的价格决定因素包括公司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负债权债务、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股权转让的对价应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在各自商业判断的基础上自行协商确定,即应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交易原则。根据上述原则,虹桥会所的股权价格不能单凭其名下房产的价格确定,故廖炳耀要求对虹桥会所名下房产进行审价的申请,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无直接关联,故不予准许。
虹桥会所的股权价格会受经营情况及市场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在账册不完整的情况下,虹桥会所转让时的债权债务情况亦无法确切查明,其转让价款到底是高还是低,亦无从比较。可见廖炳耀一方拒绝提供自己掌控的财务账册,也将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风险。因此,廖炳耀仅凭房产市价远远高于8000万元,不考虑虹桥会所的具体财务状况,又拒不提供相关财务账册,其有关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价款明显低于市价或者合理价格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无法采纳。
廖炳耀以廖东汉2005年受让UPBEAT公司股权时的价格,推定2011年3月虹桥会所股权的交易价格过低,亦欠缺比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另,国鸿公司签订《收购股权协议书》时对虹桥会所的债权债务是否明晰,涉及的是合同的可变更、可撤销问题,不会影响到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
国鸿公司受让股权后,陈志诚家属陈桂美仍作为虹桥会所办理工商年检相关事宜联系人的事实涉及的是用工管理权,与《收购股权协议书》是否系签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无涉。关于股权转让款是否实际足额支付到UPBEAT公司账上的问题,涉及的是合同履行问题,也与合同效力问题无涉,故对廖炳耀要求对方出具付款凭证等的申请,不予准许。
根据案涉《收购股权协议书》自签订到履行的相关事实,难以认定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对廖炳耀作为第三方的利益损失予以审查,以股权转让价格远低于房产的市价作为依据,却拒绝提供虹桥会所的有关账册,损失的事实依据尚且不足。退而言之,若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确实过低且陈志诚负有股东责任,也是廖炳耀通过BVI公司法途径追究陈志诚相关法律责任的问题,不是本案处理范围。
关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主张,由于贸仲裁决中指向的执行仲裁裁决的义务人是虹桥会所和陈志诚,旨在恢复廖东汉在虹桥会所的董事长职务,此与UPBEAT公司转让虹桥会所股权是两个不相干的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贸仲裁决作出以后,发生了虹桥会所股权被转让这一新的法律事实,使得贸仲的裁决丧失了予以执行的客观条件,但不足以认定此为一种逃避仲裁裁决执行的非法目的。廖炳耀所指的非法目的,更应该是指廖姓和陈姓之间有关虹桥会所财产控制权的争夺。而有关于此,无论哪一方取得了控制权,都应该遵从合法途径。由于贸仲裁决的执行客观上发生了障碍,就推断陈志诚出面转让虹桥会所目的非法,依据不足。廖炳耀在重审庭审中也表示,本案初审起诉时,廖姓尚未取得UPBEAT公司的控制权,故而先行以廖姓股东的名义提起了本案诉讼。
由于转让虹桥会所股权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UPBEAT公司的专门股东会决议,而是陈志诚以UPBEAT公司董事局主席和授权代表的身份签署,因此廖炳耀在BVI法院的诉讼中提出的对陈志诚2009年3月以来签署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对本案合同无效纠纷的审理未产生实质影响。即不影响案涉《收购股权协议书》依据中国法律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案涉《收购股权协议书》依法成立并有效,一审法院对原告诉求均不予支持。
三、二审裁判
(一)陈志诚有权代表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签订系争《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UPBEAT公司系陈志诚及亲属等人在BVI注册成立的外国法人,陈志诚及其亲属占股比例为50%,虹桥会所系UPBEAT公司在沪独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上述信息经工商登记后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第三人及社会公众有理由对前述记载事项秉持善意信赖。且廖氏股东及UPBEAT公司均确认,直到BVI法院2011年7月作出否定陈志诚修改的UPBEAT公司章程、备忘录及公司决议等文件效力的判决及命令之前,UPBEAT公司处于陈志诚控制之下。涉案股权交易发生于2011年3月,国鸿公司于同年5月完成虹桥会所工商变更登记,其后虽然UPBEAT公司内部控制权在BVI判决作出后发生变化,但并不能以在后的判决结果否定公司先前对外行为的效力。国鸿公司交易时审查了虹桥会所的对外公示信息,已尽到一般交易相对方的注意义务。
(二)国鸿公司知晓2010年4月2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刊登的“重大风险告知书”,并向陈志诚低价收购虹桥会所股权的行为,不能充分表明双方系恶意串通。
涉案股权交易系承债式收购,国鸿公司除了应向UPBEAT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虹桥会所原有的124851568.48元债务仍继续由其承担,由于原始财务凭证不完备,国鸿公司还将面临虹桥会所或有客观隐性债务未能全面披露的风险,其虽主张该交易未经过评估地产价格,属不审慎的商业行为,然陈志诚于2005年将虹桥会所母公司UPBEAT公司50%股权售于廖氏股东之时双方亦未经任何股权、地价评估手续,故国鸿公司抗辩认为其以市盈率为标准并综合考虑财务及市场风险等因素确定虹桥会所股权收购价格,并未突破一般商业惯例,具有合理性。
(三)本案无法证明存在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廖炳耀认为涉案股权交易系陈志诚为逃避生效贸仲仲裁裁决的履行和强制执行而擅自进行的交易。对此,贸仲仲裁裁决系针对廖东汉在虹桥会所任职争议而作出的裁决,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转让虹桥会所股权的行为客观上确实造成廖东汉无法恢复董事长职位的后果,但纵观涉案股权交易,相关协议不存在违法缔约内容,且由于陈志诚未参加上述仲裁程序,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院向廖东汉提起UPBEAT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该案生效判决最终已确认廖东汉尚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余额,即任职虹桥会所董事长的前提要件事实上已被推翻,故不能据此推断陈志诚具有非法目的。
故二审法院认为廖炳耀上诉主张不能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再审裁判
(2019)最高法民申1676号
廖炳耀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理由如下:
根据廖炳耀的再审申请,其认为原审判决在关于《收购股权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上,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
依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3月2日,陈志诚代表UPBEAT公司与国鸿公司签订《收购股权协议书》,约定UPBEAT公司将其持有的100%虹桥会所股权转让予国鸿公司;2011年5月,经行政审批,虹桥会所的股东由UPBEAT公司变更为国鸿公司。根据虹桥会所2005年8月26日以及2009年8月22日公司章程的记载,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廖氏股东亦在相关证明文件上对陈志诚的董事局主席身份予以确认,直到2011年7月BVI法院作出相关判决及命令之前UPBEAT公司系处于陈志诚控制之下。国鸿公司作为股权交易相对方有理由信赖其可以与陈志诚为代表的UPBEAT公司签订协议。因此,认定国鸿公司交易时审查了虹桥会所的对外公示信息,已尽到一般交易相对方的注意义务。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涉案股权交易系承债式收购,国鸿公司支付8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取得虹桥会所股权,但虹桥会所同时亦继续承担其所负债务,此种模式下,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收购价格畸低。
另外,廖炳耀认为《补充协议》是陈志诚作为UPBEAT公司方与国鸿公司恶意串通、事后补签,但未有直接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综合考虑在案证据、商业风险、交易秩序等因素,原审判决对廖炳耀否认《收购股权协议书》《补充协议》效力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五、案件研析
(一)陈志诚是否有权代表UPBEAT公司签订案涉协议?
公司作为拟制法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对外代表公司处理公司事务,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受。根据虹桥会所2005年8月26日公司章程以及2009年8月22日公司章程第二条关于“投资方的介绍”均载明,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局主席)为陈志诚,上述信息经工商登记后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在没有证据推翻前述工商登记信息前,第三人及社会公众有理由对陈志诚为UPBEAT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信息秉持善意信赖。
(二)国鸿公司低价收购虹桥会所股权的行为,是否充分表明双方系恶意串通?
判断签订合同双发是否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从《民法典》《合同法》关于恶意串通的立法理解,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则的规定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双方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隐藏于双方当事人的内心,一般需要从合同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客观行为来进行分析认定。
具体而言,民法上的“恶意”有两种含义:一是观念主义的恶意,指明知某种情形的存在,侧重于行为人对事实的认知。二是意思主义的恶意,指动机不良,即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侧重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上的应受谴责性。
从司法实践来看,债权人要以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损害其利益为由而主张无效,其主要障碍是举证问题,而因为恶意串通的法律后果比一般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更为严重,法院或仲裁机关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要求也十分严格。首先,债权人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在主观上有损害债权人的意图;其次,债权人应当证明恶意串通的双方必须有相互勾结和串通的行为。本案中转让股权的价格系当事人反复博弈基础上形成的自主商业判断,即便国鸿公司罔顾重大风险告知、无视股东纠纷并以尽可能低价收购虹桥会所股权,此系商人营利性特点所致,而非判断其具有恶意的主观标准,国鸿接手虹桥会所后已持续经营多年,收购后也已按约归还了虹桥会所拖欠的华一银行贷款4000余万元,在无充分证据证明交易双方恶意串通情形下,法院会认为轻易否定合同效力不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及营商环境的稳定。
六、解析与BVI公司交易的
法律适用与风险
1.适用法律问题
由于交易中,涉及BVI公司作为主体构建的交易模式,会导致案件可适用法律情况复杂。
(1)程序法的适用。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一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之规定,判断案件是否为涉外民事案件。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百五十九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规定”的规定进行判断。
(2)双方当事人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在内地法院进行诉讼活动时,案件法律关系的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实践中,主要看案件以什么法律文书提起诉讼,是否可以依照例如《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等进行法律关系性质的审查。
(3)准据法的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2020修正)中的相关规定,符合法律规定时,涉及BVI公司的纠纷案件应适用BVI本地法案。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若原告能够举出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确实过低且陈志诚负有股东责任,也应由其通过BVI公司法途径追究陈志诚相关法律责任的问题,而不是在本案中解决。
2.证据适用问题
案涉原告提出的BVI法庭生效判决虽未被大使馆认证,但原审法院仍然考虑了该判决所载内容,因该判决与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问题无关,法院未有采用。故可以推断,即使证据认证的形式上有微小瑕疵,法院仍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在自由裁量权内对涉外证据作出认定。详细的涉外证据解析与适用见以下本文第七部分。
七、海外及港澳台地区产生证据
在中国内地适用解读
(一)香港澳门地区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
第十六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2002)
第三条:“委托公证人的业务范围是证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证明的使用范围在内地。”
第五条:“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委托公证文书,须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审核,对符合出证程序以及文书格式要求的加章转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予转递。公司应定期(7月15日前报上半年,1月15日前报上年度)将加章转递情况报司法部。”
若是请求两处法院交换法院提取的证据则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
笔者解读
1. 在港形成证据在内地使用,首先需委托具有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进行公证认证。
2. 其次,必须同时有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章转递。
2002年2月,司法部颁布《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委托在香港执业律师办理有关公证手续。对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按照司法部规定或批准的委托业务范围、出证程序和文书格式出具公证文书。一般实践中,常见直接委托内地熟悉涉港业务的律师代为交涉将会更加高效、快捷。
(二)海外国家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
第十六条:“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四条第39项:“对当事人提供的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1)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对在我国境外形成的证据,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进行审核认定。”
笔者解读
1.海外形成的公文书证需经所在国公证。
2.海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需经所在国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详情可见每处使领馆官方网站首页关于证据公证的流程和所需资料)。
3.上述除外的其他证据都不再需要公证认证。
其中不需要公证认证的部分系对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四条第39项中,当事人有选择公证与否部分的权利一种肯定。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尤其在当今全国环境内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涉外证据认证工作变得异常困难,笔者推测,我国所有地区加入” Hague Apostille Convention”(《海牙关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港澳地区已经加入该公约,如若急需办理涉外证据在海牙公约成员国作为法律证据使用的认证手续,可以前往港澳地区办理。
附:
1.《海牙关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
https://www.jus.uio.no/english/services/library/treaties/11/11-02/foreign-public-documents.xml
2.《海牙关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 成员国及地区名单》(2021)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cid=41
3. BVI商业公司法案(最新修订版本)
https://www.bvifsc.vg/sites/default/files/bvi_business_companies_act.pdf
作者简介
2021.1.12
罗毅主任,全国优秀律师,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四川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二十余年专注于疑难复杂再审商事诉讼、仲裁、执行案件和刑事案件,细分领域深耕不辍,专业致胜,极致服务,只接擅长领域的案件。
联系方式:13908176157
13908176157@qq.com
2021.1.12
夏冬,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学士,考文垂大学商贸法法律学士,爱丁堡大学公司法法律硕士,发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才思敏捷,善于沟通交流,秉持严谨细致高效的工作作风。
往期回顾
04 再审新证据的奥秘

发现所再审业务指导委员会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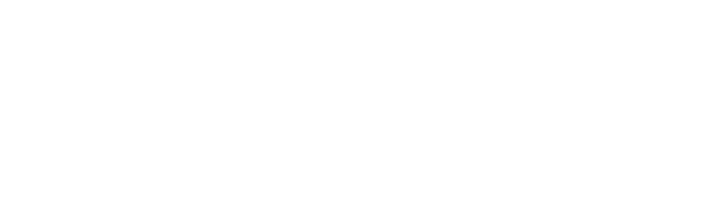
 蜀ICP备:17000577号-1
蜀ICP备:17000577号-1